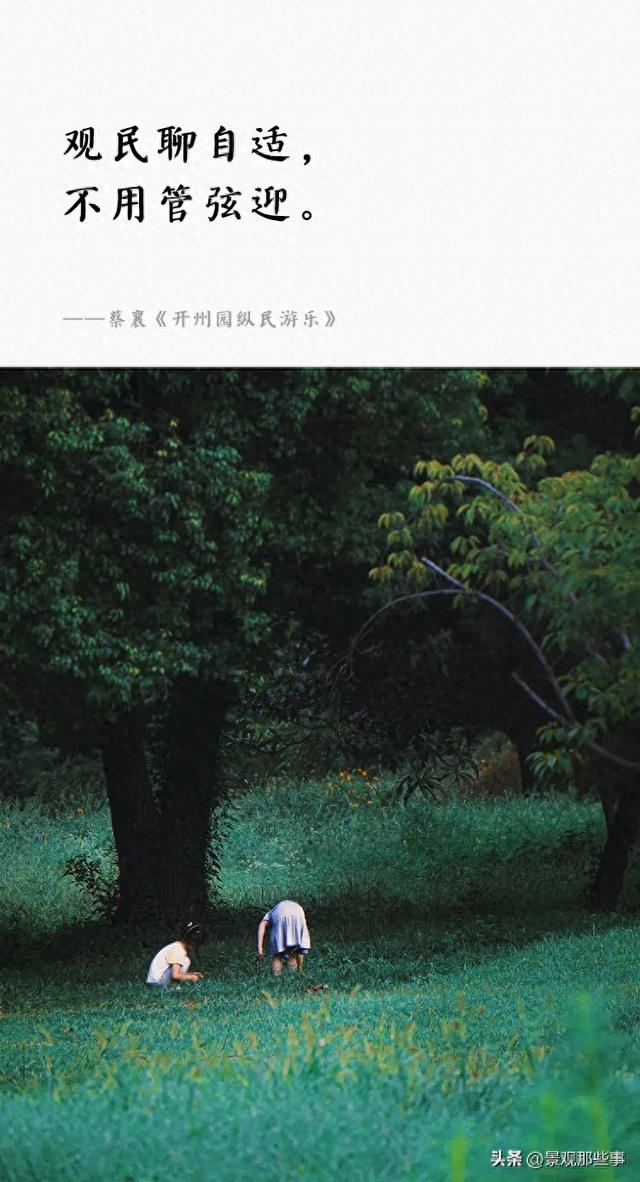
作者 |「江月两相欢」
首图 |「一直有好好吃饭」
封图 |「苏州陈杰-POTATO」
把姑苏城筛一筛,漏下旖旎的古典风情。这风情再筛一筛,我们看清了,那是枕河人家,园林小巷。倘若再从中拣出一颗绿宝石,那便是苏州公园了。我们亲切地称其为大公园。
大公园里,几声清脆的鸟鸣从林樾间泼出来,糅杂着大伙儿侃侃而谈的笑声,在阴晦天气,仿佛一缕晴朗,化在人身上,流进心窝里。难怪很多人不去熙熙攘攘的园林,却来大公园里,寻个自由,觅份怀旧。
这承载了太多回忆的地方,就像史铁生笔下浓墨重彩的地坛,无论世俗如何变迁,始终是苏州人的一方绿荫合抱的静土。

@一直有好好吃饭
翻开大公园的前世,竟可追溯到春秋时。原为春秋吴子城遗址,汉为太守署。唐宋又有增葺,该园已“春日民众可入游乐”。元末为张士诚王府,后焚毁,沦为荒地。
1908年,时值西风东渐,有人建议在此建“市民公园”。是年7月末,先在园中部荷池南建成一座城堡式两层、四面钟楼的图书馆。馆东侧临池为“东斋”茶室,西南角建西亭,园东南辟池名“月亮”,池边修廊,紫藤纷披,又植树4000余株。
园墙并非传统的封闭式高墙,是上铁栅、下砖砌的半开放式围墙。苏城沦陷,日军据园,驻兵养马,图书馆被毁,精美的铁栅栏也被日军拆去充作重制军械之用。
如今,我们依然能在大公园的南门看到原来的风貌,尤其是门口的素雅的法式石柱,虽沉默不语却流转着百年光阴。透过南门往里望去,赫然一幅焕然一新的图画。

@苏州陈杰-POTATO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大公园里建了儿童游乐园。童真的嬉笑声像是芽儿,从大公园苍老的身躯里探出来。旋转飞机、小火车、火箭等“酷炫”的游乐设施吸引了多少孩子的目光,又有多少孩子是笑着跑着进来,哭着喊着被拖出去的。
因为这个儿童乐园打烊总是打得特别早,是4点半就收工了,所以,儿童乐园的门口每天都会上演这样的场景:好婆拉着孙子要走:“走吧!人家关门哉!”
孩子呢?则是哭丧着脸:“我想再白相一趟呀!”
好婆说:“关门么哪哼白相呢?奈阿走?奈不走啊我走咋!”
在崽儿心中,儿童乐园就像是糖水味儿的春天的童话。哪个孩子愿意从童话中抽身呢?

@苏州陈杰-POTATO
入夏,则是荷花送香气。水面铺满荷叶的袖子,让碧水有了古典的灵动的韵致。团团树影在水面错节,加之草木和天云的泼墨,像是宋词和唐诗被打翻在地,那一团浓绿是辛弃疾的溪上青草,这一团疏黄是晏殊的槛菊愁烟。调皮的鱼儿时不时点出微漾的涟漪,小孩子蹲伏岸上,撒下零食屑,笑着拍拍手,抖下最后一点细屑。自然有垂钓的人,佝着身子,似是瞌睡。弥望的田田的叶子,插画一般,把四周的人儿衬成一篇朴素的散文。
荷塘旁边是一个茶室,茶水不贵,茶室里还提供苏式面。

@一直有好好吃饭
一年四季,从早到晚,大公园始终是静中有闹,你走在公园路上是一片安静,可是一拐进大公园,却是热闹非凡,有唱歌的、跳舞的、聊天的、喝茶的、遛鸟的、下棋的、撞树的。
特别在夏末初秋的傍晚,晚霞一点点卸妆,让路过的晚风粘了些柔情。鱼儿如从乐府中游出的音符,让人悠悠念起: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,鱼戏莲叶间……
园里有亭,亭外一帘翠竹,明月上挑,零星点缀,耳畔的二胡、竹笛、萨克斯、吉他、评弹交织错落,有抱膝坐着闲聊的人,有扭着胳膊跳舞的人。健身的老人和休憩的麻雀,约会的情侣和奔跑的孩子。也许独坐的人有些孤独,但这孤独只浮现了一会儿,就被冲淡了。人间百态,各种滋味,如萤火,如春花,如露珠,都酿在大公园这坛好酒里。你只是路过,闻一闻,就是苏州的感觉。什么感触呢?是柳叶飘在苏州河,小巷撑出油纸伞,是炊烟漫过青山碧水。
更不说秋末时五彩缤纷的秋叶,小朋友开心地抛洒树叶,夕阳镀金在树林,把古意的句子——“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”送到我们眼前。偌大的枫叶是大自然的调色盘里漏下的一抹朱红。一种久违的松弛感漫上心扉,树下堆积着厚厚的黄叶,我们也卸下了心中叠叠的包袱,坐在长凳上,好风澄澈,看着电影一样的光影,慢慢复杂,又慢慢简单。

@莫修-文
大公园坐落在公园路、民治路和五卅路之间,也坐落在老百姓的日常、童年、欢乐之间。它的经纬度一条是过去,一条是现在。苏州人对它有着如此强烈的喜欢,就像喜欢一个老朋友、喜欢一朵茉莉花。清静、舒适、放松,还带有家长里短,勾肩搭背的烟火气,大片的绿植点缀其中,辛松的树脂味若有似无。小喷泉里成片的鱼儿,参天的树抚摸着低矮的灌木。难怪有人说,在这里会有强烈的想要留在苏州的愿望。
如何才能看到老年以后的幸福生活呢?
松风吹解带,山月照弹琴,苏州公园是个缩影。
说明:本文首发时间2023年1月7日,首发平台:苏州园林研究所。配图已获摄影师授权,图片版权归原作者,仅限交流学习,严禁商用。摄影作者前带有@符号的,均为微博账号名称。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