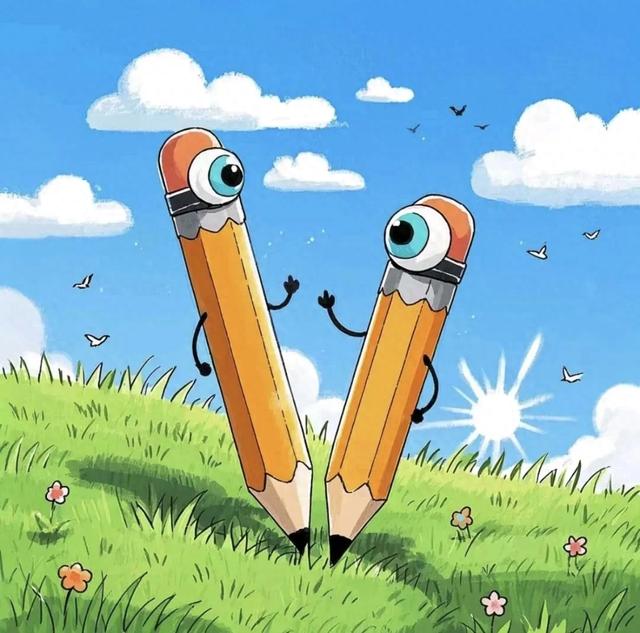
今天打完球,我去湖西路吃早餐。
早餐店位于桥北,路西。一侧是西流湖,鹭鸟在湖中的小岛上飞起落下。一侧是寺庙和村庄,人们在路上,向北或者向南。
早餐店很简陋,前台丈夫炸油馍头,妻子盛胡辣汤,老母亲趴在后面的大案板上擀面皮、包水煎包。
店前人行道上摆着几张小桌子,有免费自取的腌萝卜丝和芥菜丝。
我要了一碗豆腐脑,两元;一个菜角和三个水煎包,也是两元。
清晨的阳光从湖面上方落下来,穿过青白黄绿的法桐,斑斑驳驳的洒在人行道上,小桌子上,豆腐脑上,晃动着,看起来既真实,又不真实。
豆腐脑是洁白的,淡的,加了一勺腌过的黄豆和绿色的芹菜丁,非常爽口。
菜角是韭菜粉条馅儿的,面皮炸的酥脆。
几只小麻雀在法桐上观察了很久,现在跳了下来,在桌子周围寻觅着食物的碎屑。
这早春的季节,它们的肚子竟然吃成了圆的。虽然胖成了球,但它们依然灵巧,总是跳来跳去的。
其中的一只,竟然跳到了我的小桌子上,试试探探的向水煎包靠近。我刚一动筷子,它又敏捷的飞走了。
我拨了一点粉条在桌子上,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果然,它又飞回来了。
这是一只今年春天出生的新麻雀,在我面前机警的吃着食物的碎屑,亮晶晶的小眼睛清澈、直接。
在人类的眼里,它和其它的麻雀几乎是相同的。在麻雀的眼里,它是与众不同的吗?
它们凭什么互相吸引?容貌还是才情?善解人意还是偏词巧言?
早餐店的一家人,看起来和《清明上河图》街市店铺里的那些宋朝的人,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一千年前,一千年后,他们都会在这里或者那里,出售手艺和辛劳,养大一双儿女。为周边的人们和向我这样的过客,提供一个满足的清晨。
我经常慨叹,自己的价值不如他们,他们日复一日天长地久的满足着那么多人们,我满足了谁呢?连自己都不满足。
夏天的时候我在旅途中遇到过一个没有腿的年轻人,他坐在装着四个小轮子的木板上,一只手牵着狗,一只手攥着一把气球。
他昂着头,头发整齐的梳向后面扎起来,鬓角剃的干净利落。
他目光如炬,凛然不可冒犯。
他不乞讨,不逢迎,不卖惨,独立卖气球生活还养着一条狗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我们很多人,并没有他活的尊严。
也许因为际遇,我们活成了不同的角色,但是时间会给我们最后的公平——我们最终都会一样,热量消散,抽象成为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一个形象,统称为——人们。
斜对面的寺庙里传来了钟声,马路上人来人往,湖边有人唱戏,澡堂里有人搓背。
我在这个城市里已经生活了三十年,却只看见了一小片。城市生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老化的速度。她不停的向四周扩张着,人们不停的涌进来,让我越来越孤独。
我经常想,是不是像开封那样的城市更适合我,或者,开封也太大了,最好是洧川那样的小城。
晚上城门一关,大家都安然入睡。城墙千百年来就在那里,在人们眼力和脑力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内。
我们知道河流什么时候涨水,东风什么时候来,集市什么时候开,谁什么时候路过。
如果人生还有这样的际遇,我要做一个体力劳动者,在洎河边的土地上耕作。
麻雀吃饱喝足,也不打个招呼就飞走了,去享受新的一天。
我也感到非常开心,在春日里这个阳光美好的早晨,不仅享受了四元钱的可口早餐,还满足了一只麻雀。
结完帐我开车驶向公司,时间刚刚八点半,足够用,以前为什么那么紧张呢?
晚上看电影《浮草》。
倾斜的楼梯,敞开的窗户,窗前的清酒,窗外的屋檐,顺着屋檐垂下的雨滴,雨中的石头和芭蕉,幽静的小巷,小巷尽头的海,港口的船,闲聊的人们,海边的恋人,盼而不得的无奈,孤身上路的车站,漂泊无依的浮草,出乎意料的重逢,旧情人为你点燃的一只香烟……
晚年的小津安二郎用微微仰视的镜头,谦恭的呈现着平凡的生活,一事一物。
那些我们在宏大叙事中忽略的细节,被他赋予了极致的美,仿佛平凡的解药,役役众生的赞美诗。
我几乎纹丝未动的看完了这部电影,想像着镜头后面安静的小津。
他不急,不躁,不逢迎,不指责,把一扇窗的美和诗意拍给你看,把人间的悲伤和温暖拍给你看。
既然凡尘苦厄,不如唱一曲赞歌。
既然注定孤独,那就挥挥手上路。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