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从东部平原的喧嚣中抽身,一脚踏进贵阳,扑面而来的不是燥热,而是一股沁入肺腑的凉润。空气里裹着草木的清气,混着隐约的烟火香,像一剂熨帖的汤药,瞬间抚平了旅途的褶皱。习惯了平原的一马平川,贵阳这座长在山坳里的城,如同一位不疾不徐的老者,用山风、古意和家常滋味,向你娓娓道来何为“安住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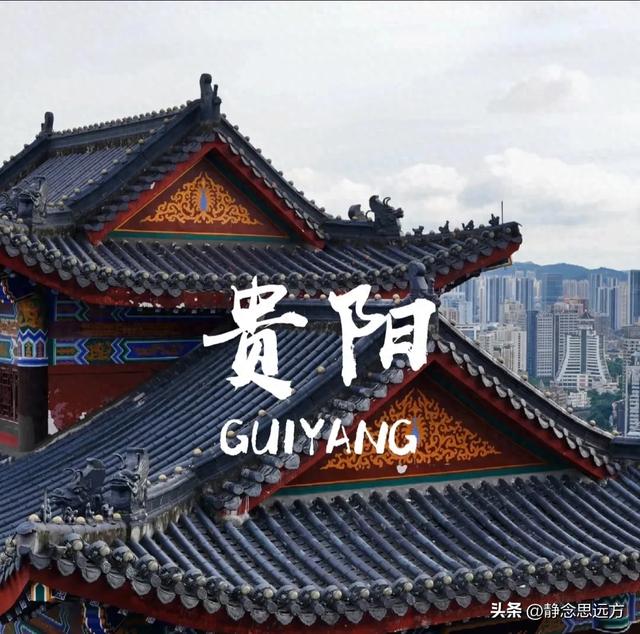
在这座“山中有城,城中有山”的地方盘桓几日,才咂摸出它的真味: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,而是时光在山石草木间缓慢沉淀的包浆。甲秀楼的飞檐翘角下,仿佛还悬着王阳明龙场悟道时的晨钟余韵;青岩古镇的石板缝里,六百年的马蹄声犹在耳畔;就连街头一碗滚烫的肠旺面端上桌,那红亮的汤色都像是蘸饱了黔地的山水灵气,透着家常的殷实与山野的泼辣。
印象一:甲秀楼,浮玉桥头的千年沉吟
穿过车流渐起的市区,南明河畔,甲秀楼就那么安静地矗立在浮玉桥头。楼阁玲珑,绿树掩映,像一方搁在碧波上的古印。拾级而上,木质楼梯吱呀作响,诉说着岁月的分量。凭栏远眺,南明河水悠悠淌过,不急不躁。常有本地的老者,拎着鸟笼或提着刚买的菜,在楼下的回廊里坐坐,一壶清茶,半日闲话。他们的眼神望向河面,平静得像看过千年风云。楼内那副“水从碧玉环中出,人在青莲瓣里行”的楹联,此刻读来,竟觉得不是写景,而是道尽了贵阳人骨子里的那份山水相依的从容。这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古建,它是整座城气定神闲的魂儿。
印象二:青岩古镇,石头缝里的烟火日子*
车子在山路上转了几个弯,青岩古镇的石砌城墙便撞入眼帘。城门厚重,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亮照人。进得镇来,两旁是依山就势的老屋,石墙、石瓦、石巷,处处透着石头般的坚韧与质朴。主妇们在自家门前支起小炉,慢悠悠地烤着豆腐果,焦香混着辣椒面的辛香在巷弄里飘散。卖玫瑰糖的老婆婆,守着簸箕里晶莹透亮的糖块,也不吆喝,笑盈盈地看着人来人往。寻一处老宅院坐下,点一碗卤猪脚配糕粑稀饭。猪脚卤得酱红软糯,入口即化;
糕粑稀饭温热绵甜,米香醇厚。店主多是本地人,操着浓重的贵阳口音,话不多,手脚麻利,那份勤恳与实在,就刻在布满皱纹却笑意盈盈的脸上。古镇的日子,就像这巷子里慢炖的卤锅,咕嘟咕嘟,熬的是家常滋味,品的是人间烟火的本真。钢筋森林里的盛宴靠排场,青岩的至味,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踏实与温情。
印象三:黔灵山,人与自然的无言默契
城中有山,山在城中。黔灵山便是贵阳人自家的大园子。清晨进山,古木参天,浓荫蔽日,山岚在晨光里浮动。石阶蜿蜒向上,常有猕猴在路边或树梢嬉戏,它们不怕人,眼神里带着一种世代居于此的坦然。弘福寺的钟声偶尔穿透林霭,悠远清越。最让人心静的是麒麟洞旁的摩崖石刻,那些不知年月的文字和佛像,早已与山石融为一体,苔痕斑驳,却自有庄严。山道上,晨练的老人步伐稳健,打太极的、吊嗓子的、提着鸟笼遛弯的,各自安闲。人与猴,人与山,人与古刹,在这里形成一种奇妙的和谐。没有刻意的亲近,也没有疏离的隔阂,只有一种经年累月磨合出的无言默契。平原的公园是修剪出来的精致,黔灵山的生机,是野性与禅意、市井与自然共生共长的原生态画卷。
平原的日子是高速路上一掠而过的风景,目标明确,风驰电掣。贵阳的时光却像这碗肠旺面,在甲秀楼的檐角下、青岩古镇的石板路上、黔灵山的晨钟暮鼓与猴群啼鸣中,被山城的云雾和市井的烟火慢煨得醇厚绵长。它不张扬,却自有千钧之力,稳稳地托着生活。出了贵阳城,舌尖的辣意久久不散,肺腑间萦绕着山林草木的清冽——那是一种沉甸甸的慰藉,仿佛在提醒行色匆匆的我们:总有些地方,能把山水的灵秀、岁月的沧桑和市井的温情,都化作家常一碗的热乎气,暖着赶路人的肠胃,也熨帖着疲惫的心魂。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