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豫东平原一路开车往东南,过了徐州,运河水的气息就浓了起来。
本以为苏北的城都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——毕竟都喝着一条河的水,说着差不多的方言。
可在淮安住了两晚,又在宿迁待了三天,我这个河南人算是看明白了:两座城的脾气,就像蒸笼里的汤包和酒坛里的烈酒,一个得慢慢品,一个得痛快喝。
先说淮安。
头天早上起猛了,摸黑去里运河边遛弯。
晨雾还没散,就听见“滋啦”一声响,循声过去,河下古镇口有个老师傅支着油锅炸茶馓。
面团在他手里转得像根细麻绳,往滚油里一放,立马膨成金黄的丝,捞出来控油时,香得人直咽口水。
“这手艺传了三代了。”老师傅拿竹筷挑起一根递给我,“战国时兵爷们带着行军,现在成了咱淮安人的早茶搭子。”咬一口,脆得掉渣,配着旁边茶馆飘来的龙井香,晨光里的运河水都跟着慢了下来。
后来去吃文楼汤包,更见讲究。
包子皮白得像宣纸,褶子捏得比折扇骨还匀,服务员说至少三十道。
“少一道,汤汁就锁不住。”她拿吸管往包子顶上一戳,鲜得人眉毛都要飞起来的汤汁就吸进了嘴里。
同桌的大爷慢悠悠剥着小龙虾,说:“咱淮安人吃鱼都讲时辰,春鲫夏鲤秋鳜冬鳊,错了季,鲜味就差着意思呢。”傍晚在运河边看放河灯,荷花灯顺着水漂,岸边有人拉二胡,调子软乎乎的,像运河水一样,缠缠绵绵没个尽头。
转头到了宿迁,画风一下子变了。
刚进项王故里,就听见“哐当”一声,青铜编钟响了,穿铠甲的演员扛着长矛从眼前走过,嗓门亮得像打雷:“霸王在此!”那股子劲儿,比咱河南老家唱豫剧的红脸还提神。
院子里有棵老槐树,树干裂得像张饱经风霜的脸,可根上偏生出新枝,绿得发亮。
导游说这树传是项羽手植,“枯了又活,活了又枯,跟咱宿迁人脾气一样,犟得很。”
中午去骆马湖边上的市集,更热闹。
渔民刚靠岸,活蹦乱跳的鱼虾直接倒在青石台上,卖鱼的大哥操着宿迁话喊:“刚出水的!称两斤?”旁边摊子上,黄狗猪头肉在大锅里咕嘟着,肉香混着甜油的味儿,馋得人走不动道。
“这肉得用乾隆老汤炖,少一分火候都不烂。”老板给我切了一大块,肥瘦相间,入口就化,配着刚烙的饼,吃得我直打饱嗝。
最绝的是晚上喝酒。
在洋河酒厂的老作坊里,老师傅掀开酒坛盖,一股醇厚的酒香“轰”地涌出来,比淮安的高沟酒冲多了。
“咱宿迁人喝酒,讲究‘干横么’——别磨叽,满上!”同桌的大叔给我倒了一大杯,酒液入喉,暖烘烘的劲儿从胃里直窜到头顶。
他说宿迁人办宴席,菜要摞三层,酒要喝到醉,“抠抠搜搜的,那叫待客?”
其实细想,两座城的脾气,不就是水和土养出来的?
淮安守着运河,南来北往的船帮在此歇脚,日子久了,就有了那份精打细算的精致;宿迁挨着骆马湖,又沾着楚霸王的豪气,风里来浪里去的渔民,自然养出了直来直去的爽利。
就像咱河南人爱吃烩面,汤要熬得浓,面要拉得长,那是中原大地的实在——每个地方的性子,说到底,都是祖祖辈辈过日子熬出来的滋味。
离开苏北那天,我在淮安带了包茶馓,在宿迁揣了瓶洋河。
茶馓配茶,是运河的温柔;白酒入喉,是楚地的刚烈。
这两种滋味在舌尖打转时,忽然觉得,咱中国的城,就该这样各有各的活法,各有各的好——就像人,有的细腻,有的豪爽,凑在一起,才是活生生的人间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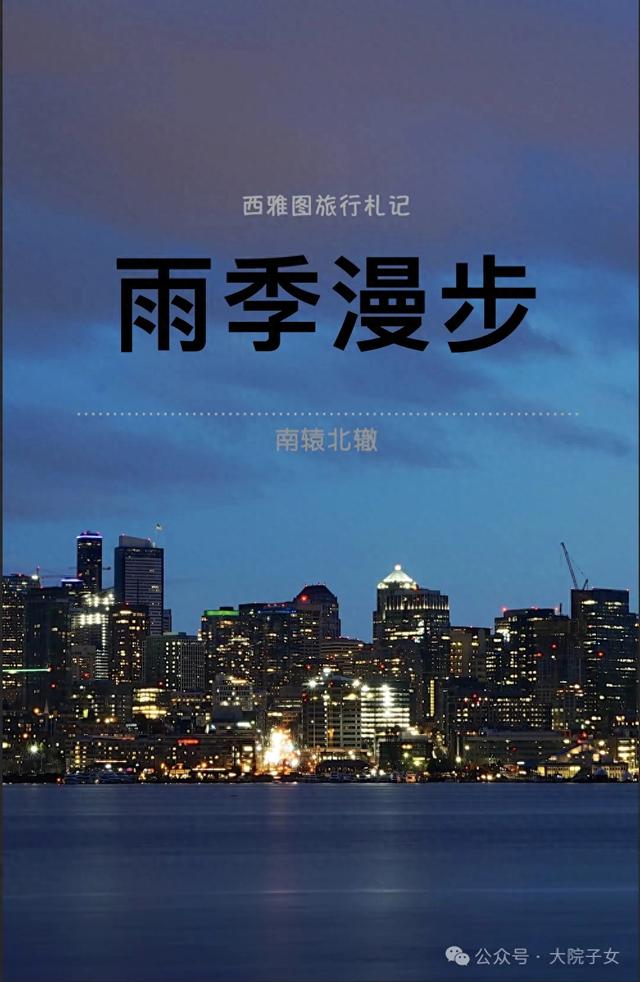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